疫情当下,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关于音量控制的群体实验。通常情况下,城市交通高峰时期的声波能穿透地表以下一公里甚至更深,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迫使人们更多待在室内,尽量减少出行。于是,地震学家注意到,他们的地下检测仪器也变得安静了。这说明地球上的古老岩石正处于沉寂状态——而这种状态,上一次出现于古老岩石形成的前四十亿年间。不仅如此,地表之上的寂静也更容易被人们感知到了。那些来自人类世界之外的声音似乎变得更为突出,不再需要太大声也能够被人们听到。旧金山的科学家就发现,如今这座城市里的麻雀的叫声变得更为柔和,音调也变低了,而这样温柔的鸣叫声,在高速公路发明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
生物学教授戴维·乔治·哈斯凯尔(David George Haskell)的著作大都是关于聆听那些消失的音律。上世纪60年代,“入世和聚神”的反主流文化成为热潮,而哈斯凯尔的作品就是对“入世和聚神”的一次严谨而科学的更新:他让我们意识到,大多数人类所拥有的狭窄的听觉范围,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使得我们与这个星球上那些伟大而丰富的乐章隔绝。2012年,哈斯凯尔出版了广受好评的《看不见的森林》,在这本书中,作者在古老的田纳西林地中选取了一平方米的森林作为整个自然界的缩影进行观察,为读者揭开了森林中令人振奋而好奇的秘密。而哈斯凯尔的新书《狂野破碎之声》(Sounds Wild and Broken)则将带给你沉浸式的体验:闭上眼睛,你仿佛置身于森林之中,所有的感官都被各种各样的背景音充斥着。
哈斯凯尔认为,地球上之所以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声音,太阳功不可没。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经历过漫长的岁月,最终才孕育了生命的碰撞。在一个寂静无声的实验室里,麦克风甚至能捕捉到细菌菌落的声音。当我们把这些声音放大,并对着细菌培养物播放时,这些细菌能通过细胞壁探测到这些声音,然后加快生长速度。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这背后的原因和原理。而细胞已经拥有这专属的愉悦乐章长达20亿年之久。最初的海洋生物并没有任何声音,直到一种“微小的蠕动的毛发”成为了促使生命走上听觉之路的进化转折,那是一种细胞膜上的纤毛,使得生物能够“听到”涡流和水流的变化,这可能有助于它们找到食物。哈斯凯尔以优美而精湛的笔触追溯了人类和动物所拥有的听觉奇迹的各个进化阶段——那是表达和接受之间无限连续的相互作用。哈斯凯尔在书中写道:“我们惊叹于春天的鸟鸣,或是夏日傍晚昆虫和青蛙充满活力的合奏,实际上,我们是沉浸在纤毛的奇妙遗产之中啊。”
蟋蟀以及它们远古的亲缘物种是这种音景进化的主要推动者。哈斯凯尔沉浸在昆虫的奏鸣曲之中,也让读者联想到了最早的乐器和记谱法:他仔细查看了保存在二叠纪岩石中的雏形蚱蜢的翅膀,清楚地展现了它们的翅膀从平整的表面逐渐进化出一种不同寻常的脊状突起,这种基因的突变使得蚱蜢能够制造并放大翅膀煽动时锯木般的声音。这样的发现将哈斯凯尔引向更广阔的视角:回声定位的进化、某些物种的“听觉感知在脚上”、贪得无厌的人类需要感受《暴风雨》中那“充满了各种声音”的岛屿,以及从鹿角做成的管制乐器到簧乐器再到数字音轨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技术在通过节奏和音乐进行创作方面都取得了进步。
最早拥有耳朵这个器官的所有物种都对新奇的事物保持高度敏感——这就像是青少年总是渴望最新的节拍一样。在动物世界的某些角落里,这方面的创新要远比其他地方丰富得多。哈斯凯尔写道:座头鲸的“金曲工厂”位于澳大利亚的海岸,新的叫声都在那块“创新区域”里产生并测试。一旦一种新的叫法确定下来,最新的座头鲸之歌将在几个月内传遍整个海洋。不幸的是,已有证据表明,这一自然奇迹近年来已遭受到残酷的干扰:鲸鱼和海豚的叫声可能会在集装箱货运船的引擎噪声中消失,求偶和求救的叫声都将被海洋噪声淹没。石油勘探机的声波测量每分钟在水下都会产生爆炸级别的分贝量,而这被认为是迫使鲸鱼——一种听觉极为灵敏的生物——离开海洋以逃避折磨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人类的噪声污染在陆地上也无处不在,所以哈斯凯尔对自然声音的研究常常带着一种告别哀歌式的基调。他去寻找荒野之地——黎明时分的森林,傍晚时分的河岸——在那里,鸟类和昆虫的声音最丰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被农药冲刷过的农田景观中,泉水寂静得令人毛骨悚然。从《狂野破碎之声》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哈斯凯尔希望通过对声音的描述来讲述我们这颗星球历史的雄心壮志,并且传递出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性。与此同时,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即便穷尽华丽之辞藻,哈斯凯尔的描述依然无法精确描绘出自然的音乐世界中那些细微的差别和多样性——而哈斯凯尔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揭示了人类正在失去的东西,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感。每当他尝试着用语言去表达他所听到的声音时,我们仿佛又看到济慈的吟诵:飞去,飞去,我要向你飞去,我在黑暗中倾听你的歌声,永恒的夜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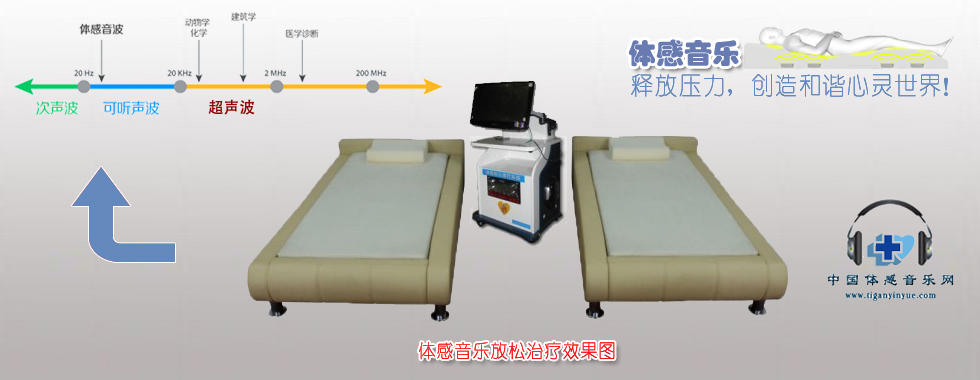

 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