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背诵过林嗣环的《口技》:“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犬吠。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一个万声竞发的绚烂世界铺陈在我们面前。
而今,身处现代都市中的我们,同样时时刻刻濡染在这样的声浪中—汽车呼啸而去的笛声,连夜赶工的建筑工地机械轰鸣声,觥筹交错杯碟相碰声,门开门关吱扭声,吵闹摔牌麻将叮咣声
告别城市的喧嚣,让我们来到野外,走近山谷、森林、草原、河畔,耳根终于清净了。然而令人心旷神怡的清净,并不意味着沉寂,保持10分钟的安静,自然造化已经备好了各式乐器,准备为你演奏一场盛大的交响音乐会。
吴金黛跑遍全台湾,忠实收录各种自然的声音。但并非每次录音都水到渠成,还得靠着她的创意与灵感,让声音说出自己的故事;就算是乡下卖菜车的喇叭叫卖声,经过吴金黛的巧思巧手,都融合成曼妙的生命组曲。曾经,她为了捕捉暮蝉的声音,误打误撞“介入”了一场青蛙三角恋,最后成为《森林狂想曲》里的意外的精彩音乐。
与天王、天后级歌手造价动辄百万、千万元的豪华录音室相比,吴金黛的录音室相形见绌却最多彩丰富,因为她的录音室无所不在:山林里的湿滑泥地、海岸边的沙滩砾石,只要有声音的地方,吴金黛就是能够创作出与众不同的特别故事。
下一次,如果你在山林野外,看到一个女孩,拿着一支比她手臂还粗的麦克风专注录音时,请随着她一起静静地体会大地的呼吸,因为那种呼吸的声音,正是大自然最丰沛的生命力呈现!
专辑《森林狂想曲》试听
第一乐章
水的奏鸣
瀑布的轰鸣,江河的咆哮,涓涓细流边的泉水叮咚。大自然中的至柔之物—水,也是演奏音乐的高手。
在这首乐曲中,发声的往往不是水流本身。中学课文《石钟山记》也是《水经》中的一篇,彭蠡的石钟山,“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声音是振源带动周围空气产生的机械波,既然“水石相搏”,那么声源当然就不只是水了。此外,在石钟山,还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坎镗之声”,水流把空气从多孔的石头中挤压出来时,封闭在细小空间中的气体受迫振动,所以这首“坎镗”之歌,水流和“多窍”大石,更主要的角色是演奏者,而空气才是发声者。
噪音中的城市
即便是绿树掩映的上海大观园里,如织的游人发出的喧哗,也盖住了自然界的声响。大都会的车水马龙之声、建筑施工之声,甚至还有各种电器的交流电的声音,在日常生活的音景中,铺陈一层噪音的“底色”。我们恐怕已经太久没有机会静心倾听大自然万物演奏的交响乐了。
“那夜,雪花飘落的声音将他从睡梦中吵醒。”秋天的夜雨,冬天的落雪,轻柔得听不到什么声音;清泉沿着势能释放的方向发出的“高山流水”之声,缠绵悦耳。但是水流还拥有另一副面孔,大瀑布处飞流直下的“天上之水”,震耳欲聋;冰峰雪崩,雷霆万钧,令人不寒而栗。
“滴答”一声
一滴水滴落入湖面,在如镜的碧波上泛起涟漪—声音的本质就在这亦动亦静的场景中呼之欲出:水滴与湖发生完全非弹性碰撞,导致的振动在水面上以水波的形式传播开去,而在空气中以声波的形式传到我们耳中,形成“滴答”一声。
水也好,雪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物相之下,“水声”的区别居然如此之大。这是因为声音的音量,取决于振源机械波振动幅度的大小,也称之为“响度”。人们规定了一个标准声音强度,各种声音的强度都和它作比较,再将比较后的值取“10为底的对数”,意思就是说差10倍就取1,差100倍就取为2,有几个零就取为几。这个值的单位定为贝尔,比贝尔低一级的单位,分贝尔,就是我们习惯上用来衡量音量的单位“分贝”。生活的闹市一般有70~80分贝,而我们日常说话的声音是40分贝左右。别以为这两个值看上去差不了多少,因为是对数关系,所以相邻1分贝的两个响度,蕴含能量相差十倍。
扯得远了,讲了这么半天,意思无非是说,能量大则音量大,滔滔瀑布携带的动能与势能,自然远远大过潺潺溪流。也正是因为自然界的水拥有如此千变万化的身姿,它才能演奏出这么一曲层次分明、张弛有度的“交响乐”。
尼亚加拉河的轰鸣
尼亚加拉河大瀑布,是美洲大陆最著名的奇景之一。它不仅以宏伟无伦的景观,给人以视觉冲击,更用振聋发聩的声音震撼着游客的听觉。从伊利湖滚滚而来的尼亚加拉河流经此地,突然垂直跌落51米,巨大的势能有一部分就转化成了巨大的轰鸣。
第二乐章
“大风歌”
原野上清风拂面,耳畔传来风的絮语;傍晚的沙滩上,海风带来波涛的咸味,也带来轻柔的回响;苍茫的戈壁上,大风挟裹着沙石,发出吓人的低吼。风是气流运动产生的,但是空气本身,却不能凭空成为振源—“风声”,其实是大地的声音。
当运动中的气流遇到障碍物,从孔洞间穿过的空气因为通过面积变小,所以得到加速,空气柱发生振动,就形成了风声。正是因为这样,古人认为声音是由“洞”里发出来的,形容寂静就说“万籁俱静”:籁原指发自孔穴的声音,所有的洞都不出声了,当然就静了。
“风言风语”造就的“魔鬼城”
在新疆的乌尔禾“风城”,风雨雕蚀形成了此处千沟万壑、怪石林立的“雅丹地貌”。这里春夏两季,常刮起大风,强大的气流在群峰中盘旋,穿过数不胜数的孔洞,发出凄厉的怪叫声。所以,这座“风城”还有一个恐怖的名字:“魔鬼城”。
当大风从魔鬼城的千沟万壑间疾驰而过,无数的石缝、石洞一齐发出鸣响,有的尖利,有的低沉,时而激昂高亢,时而声同呜咽。你也一定发现了,强劲的大风未必发出高音,微弱的气流也不一定都音调低缓—这就好比俄罗斯传奇男高音维塔斯,尽管音域能跨五个八度,却不是世界上嗓门最大的人一样:音量和音频,万物发声的这两种特征,被截然不同的原理决定着。波的频率,像一只无形的大手,主宰着声调的高低。
你联想到了什么呢?对,是光的颜色。不同频率的电磁波呈现在我们眼中,成为大千世界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低频是红色,中频是黄绿色,高频是蓝色;于是乎,有时物理学家也可以用颜色来表示声音:低频长波的男低音是红色的,高频短波的女高音是蓝色的。这种给声音“上色”的办法常用来判断噪声的类型,人耳分辨不出各种噪声有什么区别,但是一旦还原成波谱,就容易多了:波谱和白光一样,在各个频率上均等的噪声就是“白噪声”;低频多的噪声自然就是“红噪声”。
让我们还是回到风这个话题上来,音调千差万别的风声,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因为发生振动的空气柱体积不尽相同,体积小的振动得快,那么音调就尖锐,反之则低沉。大风起时,气流从这些大小不一的障碍间通过,形成各种体积的振源,合奏成这么一首此起彼伏的“大风歌”。
第三乐章
森林演唱会
森林的舞台上,正在上演一场由动物和植物同时登台献艺的大合唱—
月明星稀的仲夏夜,你仰卧草丛,凉风中四野萧然。悄然地,附近传来了舒缓的“扎织,扎织”声,渐渐地,声音节奏越来越短促,最后成为一片“织织织”的声响。这是纺织娘在歌唱。
森林的絮语
枯木折断的声音,清风拂动枝叶的声音,落叶与花开的声音,嫩芽拱出泥土的声音森林中林立的草木述说着整个大自然的语言,植物发出声音尽管微弱,但如果侧耳倾听,也一样可以感受得到。
诗经《豳风》中说:“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翅,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句中的这“莎鸡”就是纺织娘,这种昆虫抖动翅膀发声,所以才有“莎鸡振翅”之说。
昆虫“歌后”
斯螽(图1)和纺织娘(图2),是昆虫界的两位“歌后”,但是它们唱歌的风格却不太一样。螽斯是在用自己的“骨头”发声—振动几丁质的外骨骼器官;纺织娘则是通过抖动一对复翅发声。因为振源的体积几乎和它们的身体一样大,所以这些小虫才能发出那么洪亮的叫声。
听完纺织娘的振翅歌,再来听听“动股”的“斯螽”。这种碧绿的昆虫绝对是位殿堂级的歌唱家。斯螽鸣声时而高亢洪亮,时而低沉婉转,或如潺潺流水,或如急风骤雨它实际上在用自己的“骨头”演奏音乐,因为它们没有用于发声的体内器官,只能通过特化的“几丁质乐器”—外骨骼器官歌唱。
而“十月入我床下”的蟋蟀,则是通过前翅上的音锉与另一前翅上的一列小齿,相互摩擦而发出歌声的。秋后温度降低,蟋蟀的击齿就越来越慢,歌声也就随之变得沙哑、低沉。
会“说话”的植物
生长迅速的竹笋一面长个,一面发出拔节的声音,仿佛在说:“小心,别被我扎着!”(图3)堇菜类是植物早春点燃的灯火,但却是初夏唱响的奏鸣曲(图4)。大自然中的植物歌手还有很多—爆裂的豆荚发出欢快的爆破音,核桃成熟摔到地面的脆响森林实在是一个喧嚣的世界。
尽管鸣虫抢去了这场演唱会的大半风头,但是不要以为植物就能在演出中甘当看客。两片叶片相互击碰所发出的声音虽然微不足道,大风吹过,无数叶片的合奏就汇合成滚雷般的阵阵林涛。
除了借助气流发声的“树叶演奏家”,森林中更不乏唱功了得的“植物歌手”:当春雨润醒大地,竹林中常常有声音如鞭炮般响起,那是竹笋拔节的声音—翠竹之间,一颗颗竹笋争先恐后拱出地表,生长速度惊人。它们的高度一天一个模样,一个星期不见就亭亭玉立。唐代诗人李贺这样称赞竹笋不凡的生长速度:“更容一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泥。”
第四乐章
草原协奏曲
晴空下的草原上,也孕育着一场别开生面的“协奏曲”。这是鸣禽,那是昆虫,还有牛羊的鸣叫,和风吹草面,滚起的簌簌之声。这些千变万化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膜上跳动,组成一幅摇曳生姿的“画面”。面对着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朋友,我们却一下子就能区分其间千差万别。因为除了响度与音调,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特征决定着,每个乐声都拥有一副独一无二的“面孔”,这就是“音色”。
音色的不同取决于不同的“泛音”。请想象一只草原百灵的声带—它仿佛一根琴弦,被百灵鸟控制着振动,发出婉转的歌声。当这根“琴弦”以某个频率振动时,于是发出了某个音高的声音,但请注意,此时,还有一些虽然微弱得多,但不可忽视的振动,在这根“琴弦”的几何等分点上争先恐后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它们强度各异,但每一个音调都是主频的整数倍,它们就叫做“泛音”(声学上称为谐波)。正是由这些泛音伴随,空气中的这些机械波才被赋予了自己的生命,成为自然界各种具有个性的声音。
草原飞歌
还没有看到牛羊,牧歌就已经从山坡那一边飞了过来。空旷的大草原一望无垠,让任何声音都传播得更远。有时候我们觉得在屋子里说话声音更大,只是由于墙壁把声波反射回来,和原来的声音叠加在一起的缘故。
草原百灵声音婉转而复杂,这该归功于它们发达的鸣管。高等动物的鸣管声带,都是动物们自己天生的“乐器”。肌肉的作用使得鸣管或声带拉紧或松弛,来控制它振动的频率,这样就有了非常宽广的音域。如果百灵鸟只能发出独立频率的“纯音”,那它的歌唱也就不那么优美了。就如同我们用多种调味品方能烹出美味佳肴,用几种颜色进行混合才能得到酷酷的“中性色”,任何有感染力的声音都需要更多泛音元素的陪伴。
除了草原上巧舌如簧的鸣禽,植物也不是“沉默的羔羊”。酢桨草的果实是个“大嗓门”,瞬间爆裂之时,“嗒嗒嗒嗒”一阵声音宛如机枪连发;紫花地丁的果实更是位“饶舌歌手”,如果此时你恰好经过它的身旁,那啪啪的裂开声说不定能让你吓一跳。更多植物的声音我们需要屏息聆听:花朵开放与凋谢的声音,草木生长与枯萎的声音这些声息虽然微弱得被其他响动掩盖了,但确实是大自然中真实存在的。它们表征着植物繁衍的自然节律,契合着地球上万物的生息。
大自然的交响乐已经准备好就位,只等待着你入座聆听。去听,去观察,去体会吧。去度量空气的振动,去识别声音的“颜色”,去破解大自然的隐语。宇宙的奥义,就蕴含在这些平凡的声音世界之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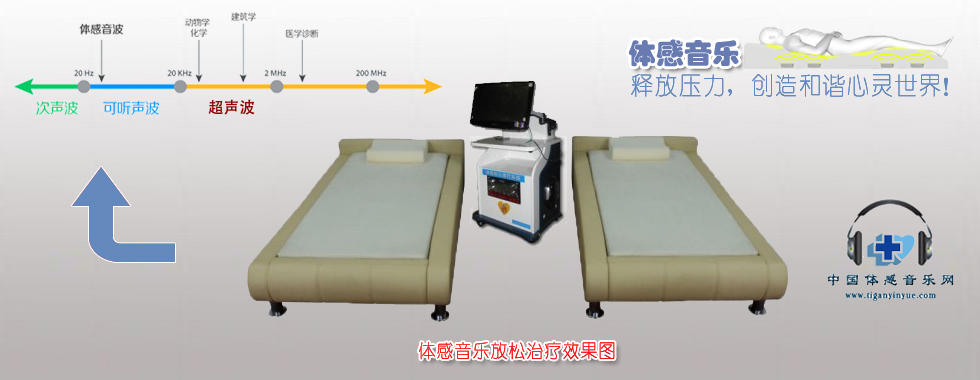

 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