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里的心理医生
某犯人一定要变性,使监狱监管面临很多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吕爽、特约撰稿何盼娅丨上海报道
10月31日,北京李某某等五人强奸上诉一案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距离3月7日李某某等人因涉嫌轮奸被依法批捕已过去了7个多月,其间这一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持续被全民围观。
曾任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犯罪改造研究所所长、对青少年性犯罪有深入研究的王仲水也注意到此案。“不少犯有性罪错的人在服刑、教养期间,其不良的性心理和性意识没有得到根本矫治,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以后重犯率较高。”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王仲水曾参与上海市少年管教所(现未成年犯管教所)对犯罪少年的矫治工作和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罪犯分类改造工作,对犯人心理和情感的关注甚为深入,他经历了心理咨询在监狱中从无到有的过程,对犯人的心理疏导有切身感触。
民国大律师吴凯声之子、中国高校中最早从事心理咨询学研究的先行者吴立岚也经历了这个过程。1996年,吴立岚接受同学王仲水的邀请,走进提篮桥监狱,担任心理咨询顾问。那时,他面对的犯人已经没有“反革命”罪名,只是普通的刑事犯。
“我让他们把手铐拿下来,还给他们茶喝,请监管人员暂时离开,否则我不能咨询。到这个房间,就要恢复他们的人性,给他们人性的对待。铐了手铐他心里仇恨着你,怎么听取各种合理意见呢?”吴立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给犯人作心理咨询时,他尽量制造一个不戴手铐、喝茶交流的谈话环境。
加刑或记过都不能改造的“问题”
心理矫正作为对罪犯改造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进入监狱系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王仲水从工厂调到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工作。他记得,有一个未成年罪犯,因盗窃一部名贵的照相机被判刑。“他有个毛病,平时喜欢和男孩子睡在一起,有同性行为。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几次,他自己写血书保证,但就是不行。”
“我感到不对劲,这不是说教就可以改好的。”王仲水说,他想到了请心理医生咨询,结果发现那个犯人有轻度同性恋心理,“在监狱里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司法处理的话就是加刑,行政处理就是记过。”
王仲水认为不应处理,而应根据他的情况加以矫正。“帮助他把性角色转过来。占领他的空余时间,用活动转移法,让他参加少管所的少年广播台,他一天到晚忙这些,晚上就正常睡觉了。”
“1987年,领导决定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引进的一名医生,专门在少年犯中尝试罪犯心理矫正。以前我们跟犯人谈话,犯人坐小板凳,我们坐椅子,居高临下。心理咨询进来后,坐姿也反映出心理要求,要创造出平等、融洽、放松的气氛。”王仲水说。
“2003年上海监狱局出台《关于加强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的若干意见》,正式把心理咨询工作建立起来。”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副主任李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2003年心理咨询室改为心理矫治科,2012年正式改称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目前的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有不同种类的治疗房间,比如沙盘室、家庭咨询室、团训室、催眠室、发泄室、音乐治疗室等。
一名犯人一定要变性
“就像医院里分科一样,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罪犯进行矫正。性犯罪、抢劫、暴力犯罪、经济犯罪等。”王仲水说。
调入提篮桥监狱工作后,王仲水的主要任务是对成年的性犯罪人员(强奸、奸污幼女等)进行矫正,“教他们练气功,让心静下来,思想净化些,私心杂念少些;搞艺术活动,让他们分辨美丑。”
“一个矫正比较成功的犯人是大学生,从小一门心思读书,社会交往能力很差,和异性接触少,与异性交往的经验都是失败的。他就把正常的性欲望转移了,找小孩子、幼女,有轻微恋童心理。”王仲水专门从监狱外面请了一位女心理专家对他进行矫治。
“比如让他看正常女青年的图片,我每天早晨早点儿叫他出去打羽毛球,采取了多方面的手段。我们帮他逐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他提前释放后有了工作、房子,结了婚,有了妻子孩子,日子过得非常好。现在是一家电脑公司的骨干人物,我家电脑坏了他也来修,带着妻子来看我。我们成了朋友。”
吴立岚认为在监狱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引入心理咨询,不仅有助于犯人的改造,也能极大改善监狱的管理。
“有一名犯人一定要变性,还采取女性姿势小便,这使得监狱监管面临很多问题。”吴立岚说,“我研究出八条标准,在什么情况下变性。我不是强迫他不许变,但是要问他具备这个条件吗?因为变性而被社会和家庭排斥,能独立生存吗?这就是以理服人,站在他的立场上想问题。”
吴立岚认为,心理咨询能帮助监狱管理者区分出有心理障碍的人,实行有针对性管理。“比如窥阴癖等问题就不是管教能解决的。司法系统引进心理咨询,还有利于犯人交代问题,帮助他们适应监狱的改造环境。”吴立岚说。
李飞介绍,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设有心理咨询牌,“如果有心理问题,犯人可以把咨询牌投入信箱,我们一周开次信箱,承诺5个工作日之内给他安排相关的咨询或心理帮助。”
“对于未成年犯人的心理咨询工作,以后会在评估方向上再加强。现在一般在犯人刚进来时做一次测量,出去时再做一次,服刑期间变化的评估却很弱。如果评估能贯穿服刑的整个阶段,有一个循证的过程,这对我们的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李飞说。
“咨询官”被当成“线人”
取得犯人的信任往往是进行有效心理咨询的关键。
“有犯人会以为我是狱方情报员、特务,这就要遵守心理咨询的普世原则。”吴立岚说,首先对当事人负责,第二是以不能超越法律为原则,第三是为可能的被害人负责,“比如,他告诉我他偷东西,我不会向司法机关汇报,他自己报告,有利于他减刑。如果告诉我他出狱后要报复杀人,那是必须要报告的。”
“有个青海的犯人叫我咨询官,让我向上级汇报,不要把他放出去,让他安安稳稳过了大年夜再放出去。他听老犯人讲,过年时监狱里有大鱼大肉,他想要享受一顿再出去。”
吴立岚让许多犯人对他说出了心里话,他还记得一个吸毒贩毒的女犯人,“她问我,老师啊,为什么初恋情人送我一个普通的金戒指,我不肯卖掉,却把丈夫的东西全都卖掉了。”
吴立岚咨询的心得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要对焦,他关心什么,我就要找什么,对焦好了才有得谈。二是触及敏感点,要钻进他脑子里,不要把自己当作咨询人。我就是他,跟犯罪人沟通就是需要这种逻辑——你不是审判者,不是一个道德批判者,不能跟他说:哎,你这么差!”
李飞曾经接触过一名犯罪人员,入监时只有17岁。一开始他非常暴躁,不能吃一点亏,按他自己讲,他是一个侠,非常讲侠义精神。“我就从这里入手,跟他讲,什么是侠,侠首先要正义,跟他讲你的正义感在哪里。另外从他的情绪入手,借助他对他姐姐的感情,多给他做工作。我想对他说的话,通过他姐姐跟他讲。现在他已经出去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他愿意吃亏了。”李飞说。
高墙之外的心理矫正延伸
针对罪犯的心理矫治,也正延伸至高墙之外。
2013年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中国日报》记者关于劳教制度改革问题时表示,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年内有望出台。同时,法学界以社区矫正代替劳教的呼声渐强。
中国的“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从2002年底起,徐汇区在全国最早开始社区矫正试点,直到2003年上海市全面推开,再到2006年全国试点,这个工作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发展过程。”上海市徐汇区司法局安置帮教工作科科长周文庆对《瞭望东方周刊》说。2012年7月底,徐汇区社区矫正中心建立,占地面积528平方米,由执法矫正区、心理矫正区、教育矫正区等三大区域组成,安置帮教工作科是该社区矫正中心的一个职能部门。
“主要是执行法律判决,规定你什么时候来报到,要做些什么,要遵守哪些方面的法律规定。请假需要我们审批,还有规定多长时间接受一次教育,参加公益劳动等。另外就是减刑、司法奖惩(减刑或者收监)、日常奖惩(警告、表扬或者积极分子),都由我们来评估。”周文庆介绍,心理矫正重在调适对象的状态,不带强制性;教育矫正主要是阅读疗法,每个月集中的教育谈话,解决困惑、了解些情况等。
社区矫正人员要定期进行心理测试和综合测评。“遇到比较多的是不适应。比如一些人曾是公务员或老板,有的有失眠焦虑,或者不服法律判决,没有办法完成角色转换。此外就是情绪抑郁,萎靡不振,对生活失去信心。还有的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危害性,对判刑的严重性不当回事儿,这尤其体现在一些青少年身上。自由散漫,报到时迟到或者不来都会有。”周文庆说。
在王仲水、吴立岚、周文庆等人看来,高墙内外的罪犯心理矫正相互配合和关联。高墙内是小社会,高墙外是大社会,都要把罪犯当一个社会人来对待,疏导他们的社会心理,使他们适应社会,而不仅仅是当作罪犯来惩罚。
“心理咨询很重视家庭和社会因素。比如,我们遇到最多的少年犯是人际关系处不好,另一个是释放之前很焦虑。有些人快要释放的时候过来咨询,说不想出去,因为不知道未来怎么办。”周文庆说。
为此上海少管所设置了家庭咨询室,“在帮助犯人的时候,也去帮助他的家庭。设计成客厅的样子,灯光摆设都有特别的设计,营造家庭氛围。”李飞说,到目前为止,他们只做了一例家庭咨询。
这个犯人父母离异,他跟了爸爸,爸爸又在外赚钱不管他。“他妈妈曾给他留了一套房子,但他爸爸作为监护人,在他还在审讯的阶段就把房子抵押了,后来生意亏损,房子也没有了。他进来的时候就扬言,出去就把他爸爸杀掉。”李飞说,给这个犯人做心理咨询,主要从亲情方面入手,也有法制教育,“把他的工作做通后,把他爸爸也请进来,进行了沟通,协商房子怎么赎回来。整体效果还是很好的,至少他不再说要杀掉父亲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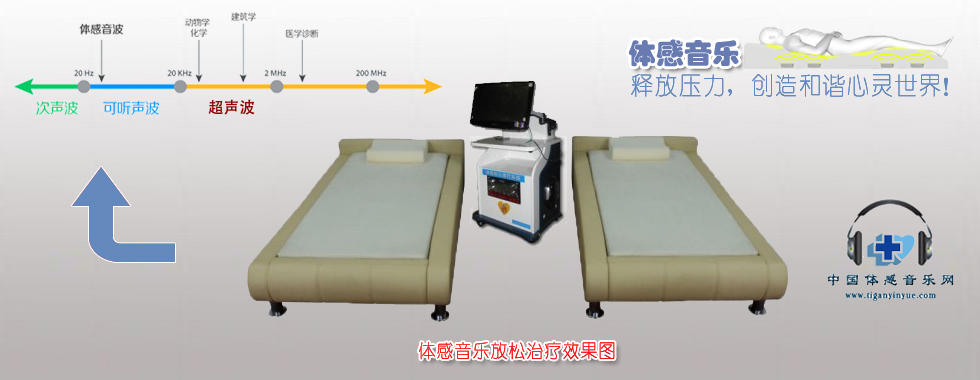

 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