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清晨,我醒来时视力特别模糊。之后,医生们很快查出了问题:我中风了,很罕见的类型。一夜之间,它破坏了我右眼眼球后面的视神经。
最糟糕的情况?左眼也会照这样发展下去,而那将使我失明。
最好的情况?稍有好转。大为好转。但我永远不会像以前那样看得那么清楚。
身边人变得清晰
的确,我视力大不如前。我视野的右侧总是蒙着一层薄雾,就像等待着永远不会升起的太阳。有时,我会弄混物体相对的确切位置。因此,当我应该敲出“live”(生活)时,我常常敲出“love”(爱),而当我应该敲出“love”时,我又常常敲出“live”。在键盘上,字母“i”和“o”是相邻的。而且我对深度的感知会变得不太正常。在我中风后的几个月里,那些让我给他倒葡萄酒的人们可以证明这点。我会倒得溢出他们的酒杯,把酒洒到他们腿上。
我不倒酒了。我感到懊恼。我生活在焦虑中,希望我的左眼能挺住。它的确挺住了,还出现了一种医生们没有预料到的幸运情况:一点点地,我身边的人们变得清晰起来,我的意思是,我逐渐看清了他们的恐惧、挣扎和胜利。
“飞机失事,义肢,失去了8岁的儿子。”一位曾和我在曼哈顿同一家健身房锻炼的作家遭遇了这些。这是对一个悲伤故事的简要概括。开飞机是他的一项爱好,他开的飞机坠毁时,机上唯一的乘客——他的独子——死了。他差点失去第二条腿,在康复中心度过接下来的五个月。这一切我不是从他本人那里知道的,而是从他的熟人那里了解到的,而且是在与他进行了多次乐观热情的聊天后才知晓的。在与他的聊天中,他没有流露出任何迹象。我感到震惊和惭愧。
“令人衰弱的头痛、不间断的尖叫、频繁的自杀念头。”这是一位曾经向我吐露秘密的名人所遭遇的一切,而且我怀疑,任何觊觎这位人士财富和名气的人都不愿意与他互换身份,至少不愿带有这些条件。这些内情让我肃然起敬,因为这些揭示者还在砥砺前行。
有些挂在别人身上的标签我能轻易读懂,因为现在我对世界的解读截然不同,有些是别人挂在我身上的,他们了解我本人的标签(“视力受损,可能失明”)。我不必强迫有烦恼的人分享经历。这些会在不经意的时候一点点流露出来,而我只需保持足够敏感,抓住细节。
我会继续留意以前或许会忽略的评论,并将一些对话进行下去,而过去我或许会匆忙结束或绕过这些话题。在我曾参观并发表演讲的一所大学里,有人提到了校长夫人的健康问题;后来与她见面时,我温和地问及相关事情,并了解到,在其身边的人也不知道的许多日子里,她挺过了背部剧痛。
拉斯维加斯一家餐厅的经理认出了我,而且是在看过我写的自己视力危机的文章之后。他向我吐露心声说,自己有终身性视力问题;后来我又与他联系,并了解了他的全部故事。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关于磨难和成就的故事。这是关于毅力和正向思维的一课。它让我正确地看待自己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困扰。
从痛苦中领悟
在我看过和读过这么多之后,我从别人隐藏的秘密和经受的痛苦中领悟到了启示或者说寓言。著名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2019年自杀时,我感悟到了这些。
我曾经采访过克鲁格。他的举止让人愉悦,采访也舒服自在,这让我大感意外。采访通常让人有压力,但那次经历与众不同。
我要告诉你们我新闻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秘密,一个预示着影响我余生的自我怀疑和怯懦的秘密:在我拿起听筒给采访对象打电话之前,我必须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我得深呼吸几次。我担心自己问错问题,或者没有问对问题。担心自己笨嘴笨舌,提问的方式让人尴尬。如果我要采访的对象颇有名气或德高望重、资历深,我就会被吓倒。上午11点的采访许多是在11点02分开始的,定于下午3点的采访许多是在3点03分开始的。这并不是因为我马虎拖延。这是因为我需要用这些额外的时间来进行深呼吸,这些时间非常宝贵,值得我为自己的延误道歉。
但我记得我是按时打给艾伦·克鲁格的。我们在通话前来回发了几封邮件,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让我平静下来。作为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曾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治下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提高最低时薪所造成的影响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他确定了这不会导致招聘减少和就业率下降。
吸引人的是,他还利用数据得出了有关疼痛和幸福的结论。他发现,失业不仅仅会造成情绪困扰。寻找工作的男性还会提示身体上的疼痛,服用更多止痛药。至于幸福感,根据他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增强幸福感的最佳方式之一是与朋友共度时光。他经常参加社交聚会,克服工作一周后的疲劳。
我2014年底找他交流。当时我正在写一本书,讨论美国人对普林斯顿大学等顶尖大学的情结。恰巧那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克鲁格和数学家斯泰西·戴尔研究了大量上精英大学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数据,他们认定这一经济效益被高估了。克鲁格的电邮信箱地址是公开的,所以我给他写了封电邮,询问他是否愿意与我在电话里聊聊这项研究。作为破冰话题和说服手段,我提到自己曾短暂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迅速回信说:“你随时可以在我的课上讲课!”他很乐意讨论自己的研究,但他道歉说,当时不行,因为他在意大利,而意大利之行后,他会有几天很忙,忙女儿大学毕业事宜。他问道:“我们可以约在下周三或周四谈谈吗?这个时间会不会太迟了?”我清楚地感觉到,如果我说等不及,他肯定会想办法配合我的时间。
我告诉他,下周三我可以。后来,我们进行了交谈,他太有礼貌了,太令人愉快了,太有耐心了,太棒了。他谈到了我的书,那本书将于次年出版。每当我在新闻中看到克鲁格的名字——我经常看到,因为他对记者非常宽厚——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甚至有点迷上他了。提及他的文章旁有时会配照片,那些照片显示,除了才华横溢和善良外,他还很英俊。有些人拥有一切。
克鲁格去世后,奥巴马发表了声明,回忆称克鲁格拥有“永恒的微笑和绅士精神——即使是在他纠正你的时候”。曾与克鲁格一同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写道:“我还算了解艾伦,但从未发现任何可能发生这种事的迹象。”
接替克鲁格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贝齐·史蒂文森发表了一连串推文。其中,她提到了克鲁格对疼痛的研究。她写道:“如今,我知道他也很痛苦,也许是为了转移自身痛苦,他思考他人的痛苦。”
她还说:“事实是,我们所有人的痛苦都比外界知道的多。”(胡婧译自2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原题为《视力下降让我看得更清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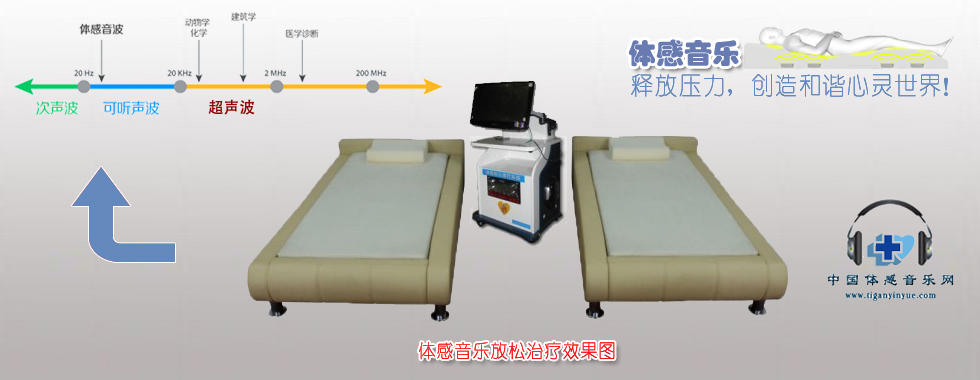

 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