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首发于2018年2月1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抑郁症冰山》)
世卫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早在2009年,《柳叶刀》论文显示,中国需要心理健康服务人群高达2.48亿人,而仅有4.9%得到正规治疗。
“为了逃开那头怪兽,你一直跑,一直跑,但是这样是没用的,你不能一直用后背对着它;你要勇敢地转过身去,才能看清那头怪兽的本来面目。”
茧居少年
四五年前开始,温州康宁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叶敏捷发现诊室里多了一些特别的求医者。
他们是和叶敏捷年纪相仿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前来求助。这些孩子不上学、不恋爱,在原本充满青春活力的年龄,却退缩到自己房间里。有的隐蔽在家中几个月甚至几年,年满二十岁之后,依然足不出户、与世隔绝。
“就像一个把自己拼命裹在茧丝里的幼虫,失去了应有的生命力。”叶敏捷说,唯一与外界接触的时刻,是这些孩子出来拿父母放在门口的食物,拉开房门取托盘的一瞬。迫不得已时,也只通过手机信息或字条与家人交流。
随后,他发现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中也报告过大量案例。2016年9月,日本内阁府估算,全国15-39岁的人群中,约有54万“茧居族”,这些年轻人通常来自中产家庭,男性居多,开始茧居的平均年龄为15岁。
日本医师齐藤环是这一现象最为权威的研究者之一。在这一问题尚不严重的二十世纪末,他就预见这会成为发达社会的严重问题。齐藤环是这样定义的:三十岁以下青年,在家足不出户,与社会互动脱节的情况持续六个月以上,且主要成因并非生理引起的精神疾病。南方周末记者查阅文献发现,西方国家将其命名为“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但也有专家认为这不属于某种单一疾病,而和多种精神心理障碍有关。
叶敏捷说,大部分茧居少年是因为恐惧人际关系、内心压力过大或各种焦虑心理。有的达不到抑郁症的程度,但内心说不出的挣扎不安,让他们无法转变到自我负责的成人状态,从而退行为需要照顾的儿童状态。
糟糕的是,很多父母为了面子,往往甚至数年之后才走进精神心理科。而劝说孩子就医则更难。叶敏捷的一位好友是中学校长,直到儿子已经在家茧居三年才向他求助。
16岁的欣悦是叶敏捷的病人之一,重度抑郁伴有自杀倾向。刚接触这个孩子的时候,连叶敏捷都感到“十分绝望”。
欣悦出生后,父母工作太忙,一直是爷爷奶奶照顾。小学之后,由老师代为托管。到了初中,她已经变得非常叛逆,上网成瘾、厌学,并不断与父母产生冲突。此时,父母终于意识到孩子出了问题,不顾一切地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开始严格管教。但却适得其反:孩子越来越沉默、抗拒、消极。最终,欣悦花了一年的时间,偷偷收集重金属汞,存够剂量后,用静脉注射的方式自杀。叶敏捷被这样的逻辑缜密、思维清晰的自杀方式吓到了。
抢救回来的欣悦开始了住院治疗,但几乎不与任何人交流,只是无休止地看着手机。
“要打破这个系统,必须要家庭一起参与治疗。”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主任李艳说,最大问题是家庭单元缺失,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感情链接,造成了孩子在社会适应、人际关系和文化上的冲突不断。
“逛医”族
和不愿意就诊的茧居少年们不同,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温附一院)主任医师何金彩则看到了另一群特殊患者。
30岁的张青已是半年内第四次就诊了。不明原因的头痛、心慌、胸痛,让她每一次来都会带上比前一次更厚的检查单——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异常”。何金彩尝试着给她加了一种名为奥沙西泮片的抗焦虑药物,症状竟明显缓解了。
作为神经内科的医生,她的治疗对象原本应是脑血管等疾病,然而最近十年,她发现,门诊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患者,和张青一样,走上了难以解释的“逛医”之路。
这些病人有着明显的身体不适,但各项生物学检测均不能发现异常。病人反复“逛”医院,在不同科室、专家之间徘徊。这不仅让病人痛苦,也让家人苦恼、医生手足无措。
“我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一现象。”何金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类病人属于典型的心身障碍,多为急性焦虑、惊恐发作时产生的生理反应,医学上也称为“心理问题的躯体化”或“心身疾病”。
2004年,何金彩力主在温附一院设立心身医学科,接受这些反复“逛医”的患者。一开始,病人很抗拒从精神心理的角度听从医生解释,但消除症状又是他们最为渴求的,只能试着吃药,结果意想不到地好了。
有别于典型的精神疾病,这些病人不是或较少以焦虑、恐惧及情绪变化等心理化的方式呈现,而是以头痛、胸痛、心慌、呼吸困难等躯体症状的方式呈现。现代医学一般把心身疾病分为三类,即植物性神经系统障碍、代谢和内分泌障碍及过敏性疾病。心身疾病的临床特点常常是有阶段性的,症状高潮期过后便是症状的减轻乃至消失;并且症状出现和消失的次数与患者所体验到的心理紧张量有对应关系。
事实上,在国外超过50%的初级保健诊所患者会有焦虑、抑郁、躯体化症状。国内多中心大样本的调查也显示,焦虑和抑郁障碍在综合医院就诊的病人远高于其他病种。1986年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的研究发现,37.2%的患者有身体不适,但无其他任何异常。而在美国罗切斯特地区以身体症状为主诉的比率则为22.9%。近20年,非洲、印度等其他地区的研究都报告身体症状与疑病症皆为抑郁障碍的主要症状。
而研究者发现,同样是抑郁症,中国人多呈现躯体症状,如出现头疼、失眠等躯体上的不适,而美国人则多表现出有关存在意识方面的忧患,比如觉得活着没有价值等。“这和东方文化也有关系,中国患者更习惯陈述身体症状,希望解决身体不适。”何金彩说,因此很多病人宁愿来神经内科就诊而不是精神科。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提到另一个十分典型的疾病也与此有关。“中国人找不到病因就爱称是神经衰弱,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病,国外早就不说了。”
神经衰弱原是形容慢性虚弱、易激怒和疲劳为特征的病理心理和病理生理状态。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精神病学家们就开始争论神经衰弱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病种。而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将这一概念删除后,美国停止使用这一疾病类别,代之以抑郁症、焦虑症等分辨性更好的疾病。
但在中国,神经衰弱始终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发现这个重大区别的正是徐一峰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时的导师——著名的精神病学和人类学家克雷曼·凯博文。
20世纪末,克雷曼对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科某一天的门诊病人诊断情况进行统计,有19%的病人被诊断为神经衰弱,而只有1%的病人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后,克雷曼对被中国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的100例患者进行研究,按照国际诊断标准,有93%的患者可以被诊断为抑郁症。更有意义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经过抗抑郁剂治疗后,抑郁症状都得到了缓解。
“中国医生所诊断的神经衰弱,绝大多数就是美国医生诊断的抑郁症。”徐一峰说。
被剥夺的劳动生命力
在普遍概念中,抑郁焦虑就是“不开心”。但其实,持续的情绪低落只是冰山一角。抑郁症最可怕的是不可控的机体机能退化,以及不可控的思维认知的改变。网络上,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是这样描述的:抑郁症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
宁波姑娘小冉住院后写下了自己的生病状态:“去年9月起,我开始没由来地对一切事物丧失兴趣,包括热爱的音乐、电影、书籍等等。走进电影院像是去上坟,音响覆盖了细濛濛一层灰尘,木心的诗集也长久地停留在了同一页。”
像很多人一样,她以为是天气变化引发的倦怠,没有在意。但后来,她的身体机能开始明显退化。胸疼、头疼开始侵袭;记忆力、思维明显减退。有些时候会莫名涌出泪水,更多时候,就是发呆或是昏睡。直到确诊重度抑郁必须住院后,小冉才明白:不是只有精神分裂症等重型精神病才需要住院,精神病院也不是“关疯子”的监狱。
一个月前,国内最大的民营精神专科医院温州康宁欲在A股上市,引起社会波澜,其招股书称:“中国精神病患的数量在快速增长”。早在200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人是精神障碍患者。
同年,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关中国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患病状况的论文称,在中国四个省市调查的各种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7.5%(定义为一生之中至少一次需要专业人士帮助/诊治),需要心理健康服务人群高达2.48亿人,而仅有8%寻求过专业帮助,4.9%得到正规治疗。
而在全球范围,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100万人,抑郁症的发病率是11%,即每10个人中就可能有1个抑郁症患者。
原广州脑科医院精神科医生、昭阳医生的创始人林昭宇把精神障碍人群用一个金字塔结构描述。塔尖是最严重的六种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这是被看见且被社会重点关照的部分,但只占据全部人口的1%。余下的2.3亿人——如同水面之下的庞大冰山若隐若现。
林昭宇解释,这部分冰山人群里,有一些是需要终生服药和治疗的重度精神障碍患者,但更多的是及时就诊就能恢复正常工作生活的普通人。
南方周末记者跟随叶敏捷在他所在的抑郁症治疗中心走访,许多病人在服药后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你看得出他们是患者还是家属吗?”
四十五岁的江生原先是温州一个颇有名气的民营企业老总,创办过多家公司,资产数千万,但焦虑症让他过往的财富、名气和成就都变得毫无意义。现在他每天在病房里踱步,唯一想的是,世界上哪里有能医治他的“神药”。
冰山之下,这样的患者无数。“80%—90%的抗抑郁药物是在综合医院开出来的。”何金彩说。
而像小冉记录的状态在国际上有一个专有名词——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作为评价各类疾病总负担的一把标尺,DALY指的是某种疾病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包括因早死所致的寿命损失年和疾病所致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两部分。
2017年4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黄悦勤教授公布了一项覆盖全国31个省份、三万多人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59%,抑郁症终生致残率为49.67%,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心境障碍造成6年健康寿命年的损失(DALY),在各类精神障碍中排列首位。
这也印证了2016年5月,《柳叶刀》上刊登的三篇论文的结果:中国占据全球精神疾病负担的17%,印度贡献了15%。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负担比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加起来还要大,受资源匮乏和偏见影响,数百万人没有得到治疗。
损失的不止是生命年限。
世卫组织还主持了另一项研究,计算了从2016年到2030年的15年间,36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治疗费用和健康结果。研究表明,对抑郁症和另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焦虑症的低水平认知和治疗,将导致全球经济每年损失上万亿美元。——像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家庭、雇主和政府都不能幸免:个人不能工作时,家庭在经济上受损;员工生产力下降或不能工作时,雇主受损;政府则不得不负担更高的卫生和福利支出。

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的金字塔分布图。(农健/图)
谁来帮助“破茧”
无论是“茧居”还是“逛医”,大多数精神病患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容易。
叶敏捷曾在心理治疗时,接触到一个永远在滔滔不绝说希腊神话故事的孩子,目的只为拒绝接受医生的谈话治疗。“那个孩子后来告诉我,心理医生不就是想和我聊天吗?我不停地说,他就没法说话了。”
住院后的欣悦则一直不言不语。一天,叶敏捷例行查房时,听护士说,小姑娘很喜欢写诗。他便试着鼓励欣悦将一篇题为《述梦》的小诗发表在科室的公众号上。
欣悦同意了。随后叶敏捷开玩笑问,“要不要给你稿费?”她摇摇头,笑了起来。
“那就像是她生命中出现的一抹亮色,让之前那个黯淡无光的生命有了活力。”医生们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感到了莫大的安慰和希望。
抑郁症往往是慢性病,具有复发和再发的特点,但同时又是可治疗的。遗憾的是,根据上述《柳叶刀》论文数据,因为病耻感和不了解,中国仅有不足6%的焦虑、抑郁、药物滥用、痴呆症及癫痫患者寻求过治疗。相比之下,发达国家该比例达70%甚至更高。
这和中国专业医生严重不足有关。根据2015年卫生统计年鉴数据,中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两万七千余人,心理治疗师五千余人,总计只有三万多。中国精神卫生医护人员数量上升缓慢,与世界同属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每10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7人、精神科护士5.35人的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里面还有很大水分。”徐一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4%的中国注册精神科医生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29%的人只有大专教育证书。精神卫生服务人员社会地位低,福利待遇差,整体素质偏低。他在哈佛医学院学习时的导师就极不认可这一数字,理由是“中国的医生远远没达到专科医生的水准”。
另一方面,中国卫生总投入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卫生部门对精神病医院的拨款仅占2.3%,基层精神病院则更少。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介绍,仅有中国人口1/4的美国,精神科医生多达3.8万人,这还不包括20万临床心理治疗师。
陆林说,“1个精神科医生,要配备3到5个心理治疗师,组成一个团队,这才是科学合理的。因为心理疾病非常复杂,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可能要很多次治疗才能使患者好转,直至康复。”
叶敏捷也深有感触,他面对的“茧居”少年们,主要不是靠药物,而是多次的家庭心理治疗。2017年2月14日,叶敏捷带领康宁医院的十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成立了“茧居工作小组”,希望通过设计调查方案和干预流程,让更多的孩子破茧而出,走出困境。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撒旦的情歌》里写道:“为了逃开那头怪兽,你一直跑,一直跑,但是这样是没用的,你不能一直用后背对着它;你要勇敢地转过身去,才能看清那头怪兽的本来面目。”
(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欣悦、张青、江生为化名)
(感谢国际记者中心ICFJ对本期精神健康选题的支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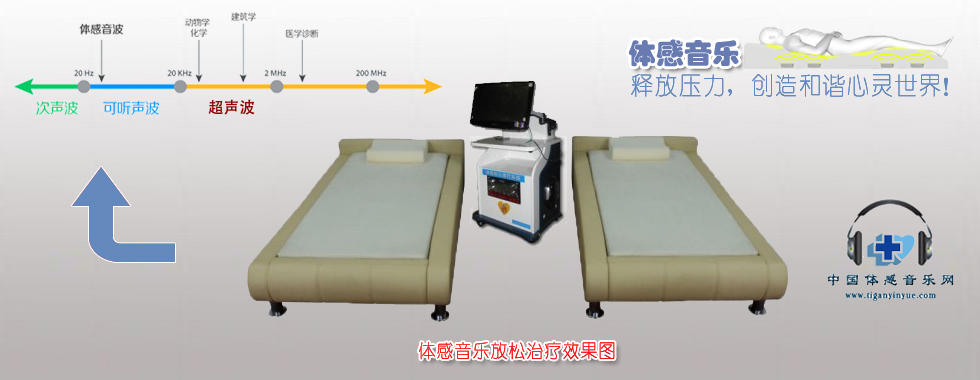

 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